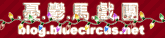« 張雨生 1992 台南 | 回到主頁面 | My Albums Of 2019 »
2019-04- 5, 10:55 PM
爺爺

爺爺走的那一晚,我整夜沒有睡好。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整個人浮浮躁躁,好像心裡積了什麼事情。心事,確實有一兩件,但應該都是好的:就在昨天,我完成了第五十座台灣百岳,而再過一天,就是我四十歲的生日。
也許剛下山,身心仍滯留在高海拔地帶,亢奮的情緒也尚未平復下來,一時半刻不是那麼容易睡得著。也許我對即將到來的四十歲有一種期待之情,整頓覺睡得朦朧又恍惚,一個夢都留不住。
我在早晨七點驚醒,下意識滑開手機,發現Line的圖示浮現出紅色的未讀訊息標記,我內心有感,南方出事了。人在高雄的堂姊在家人群組向大家通告,爺爺已經不行了,此刻正躺在高雄的家裡,法醫下午會來相驗。這天是冬至,一年中黑夜最長的一日,也是我三十九歲的最後一天,頂樓窗外,台北晨光和煦。
包括我在內,爺爺共有六個內孫、兩個外孫,每個人的名字都是他取的(我們家族流傳著一幅二十字的族譜,我這輩是「德」字輩),而八個孫子中,我是年紀最小的一個,從小和爺爺一直像是忘年的朋友。他選擇這天離開,彷彿是讓他最小的孫子就留在三十多歲,依然是個孩子。
我在心裡預演著這一天少說已經十年了,坐在床上,我沒有哭,只是先傳訊息給幾個第一時間想到的人--前女友、大學的哥兒們、其他剛下山的登山隊成員。我在訊息裡寫:「爺爺今晨走了,享壽100歲」接著就把手機關機。我到廁所盥洗時一邊想著,昨天睡前聽的最後一首歌好像是平克佛洛依德的〈Wish You Were Here〉,我接著想,上回見到爺爺是什麼時候?
其實並不是太久以前,是九月底的中秋節,我搭高鐵回台南,再開家裡的車載爸媽到高雄和爺爺吃了頓午飯。回想起來,當天的一切都是那樣的尋常,每個環節都遵照著我們早已習慣的腳本:媽媽在預定出發時間的前十分鐘就吆喝我和爸爸該出門了,我從車庫倒車,她捧著一瓶剛泡好的熱茶坐到後座,另一隻手提著一袋柚子和月餅;爸爸坐在副駕駛座,身上是這陣子最常出勤的那件襯衫,他總在車子開出巷子前略顯驚慌地回頭確認鐵捲門已經關上。
星期一上午,南下高速公路的車流不多,這是一條四十年來我們一家人來回往返過成百上千次的路線,不同的是,手握方向盤的人從爸爸變成了我。我習慣下交流道前問身旁的爸爸:「是這個出口沒錯吧?」我們的車便駛下交流道,行經固定的路途停在爺爺家門口,準備和他再過一次春節或元宵或端午或誰的生日,或只是單純想回去探望他。
奶奶過世後,爺爺自己又豁達地活了二十年,漸漸地,他在世界上已經沒有朋友了,和他關係最緊密的是一名照顧他十年的菲律賓移工艾達,就像爺爺晚年遇見的另一個女兒,也是我們家族的守護天使。
是她來應的門,我和爸媽走入社區的庭院,時序已經入秋,南國依然那麼的溫暖,那麼適合一對老人和看護在這裡日復一日過著平淡安穩的日子。爺爺會坐在客廳用放大鏡讀著他的《聯合報》,聽見開門聲會很有元氣地說:「哦!回來了!好好好。」待我們坐定,他會放下報紙,和我們閒話家常,我會趁這個時候環顧這間承載著家族記憶的房子,也聞一聞爺爺生活的味道。
餐桌上的菜飯,茶葉的殘渣,他要艾達去市場買回來插在瓶子裡的花卉,還有各種維繫一個九十多歲老人身體機能的保健藥品,那些藥的氣味。除了衰老與退化,爺爺的身體大致上仍是健康的,他一手字寫得比我還工整有力。
十一點三十分,爺爺會請艾達開始幫他穿鞋、戴錶、戴墨鏡,我們去了那間最常去的客家館子,爺爺照例點了一份肥腸,淺嚐一兩片,一邊自我叮嚀道:「不能吃多!」午餐過後,我們會回爺爺家再喝一杯茶,稍微坐坐,然後就開車回台南。
那天如果有反常的地方,是我和爸媽臨時決定睡一頓午覺再走。我到二樓從前爺爺和奶奶的主臥室睡了一場好深好沉的覺,是那種在極度安心的狀態下才有辦法進入的深眠。醒來後,覺得人生好像南柯一夢,而且夢到了國中時最好的朋友。
記憶回溯至此,我發現那天最反常的地方了,我們要離開時,我和爺爺說再見,他沉默了,這是三四十年來的第一次。眼看爸媽已經走到院子穿鞋,我回身再和爺爺說了一次再見,這次緊緊握住他的手,但他依然沒有回話,只是抬頭看著我。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那就是告別的時刻。
法醫開立的死亡證明,白紙黑字是這麼寫的:「急性心肌梗塞,屬自然死亡,201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六點二十分。」分離二十年後,爺爺到天堂牽起了奶奶的手。
爺爺是台灣島上幾乎凋零殆盡的「大時代」人物,民國八年出生於湖北武漢,一輩子沒見過親生父親,從小由叔父養大,稱自己的親生母親為伯母。二十四歲那年進入空軍服役,任補給中隊副中隊長,歷經西安事變、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國府遷台、八二三砲戰、台灣經濟起飛、民主化、政黨輪替,直到才剛席捲高雄的韓流(他在投票日一早就坐著輪椅去行使公民權利了)。
相較於我的偶像楊德昌、大衛鮑伊、約翰藍儂、楚浮、傑克凱魯亞克、安迪沃荷、路瑞德、李歐納柯恩、金庸,爺爺比他們都更早出生,然後更晚離開。他在這世上活了一整個世紀,自己就是一個時代。
為了彌補被戰火剝奪的學生年代,爺爺退休後花了十九年修習空中大學的課程,一個外省老兵,每天這樣孜孜不倦、皓首窮經,最終修得150個學分,豐盛得足以讓他領取人文及社會雙學士學位。台北的畢業典禮,是爺爺第一次見到他的「同學們」,合照時他穿上學士服、戴黑方帽、胸前別了一朵塑膠花,整個人像一尊佛,與校長老師坐在第一排。那年,爺爺已高齡八十六歲。
我在各方面都受他的影響很深,譬如家中的東西要擺放整齊,對未來保持著一種樂觀,喜歡到處趴趴走,而且每天寫日記。我遺傳到爺爺鼻子的形狀,身體裡流著他的血。爺爺以身作則,總讓我覺得當一個讀書人,一個寫文章的人,是值得驕傲的。
我第一本書出版時,他來參加了高雄場的新書發表會,第二本時他沒辦法在外頭連續坐上一兩個鐘頭了,依然在發表會結束前到場和我握手,說聲恭喜。又過了四年是第三本書,爺爺的身體再也禁不起長距離的移動,但腦袋仍是一清二楚,活動前幾天他用智慧型手機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不能到場,祝一切順利。
幾天後我的電話又響了,爺爺在話筒那頭說,他已將整本書讀完,並在扉頁寫了幾行讀書心得,請爸爸翻拍給我。我在高鐵上把那張照片點開,看見蒼勁的筆跡寫著「已讀按讚」,覺得自己擁有全世界最酷的爺爺。
九十六歲那年爺爺決定受洗,其實已在安排自己的後事。告別彌撒舉辦在爺爺家附近的天主教堂,我們和神父、祭司、教友和其他來送陳老先生最後一程的街坊鄰居一起唱著〈奇異恩典〉,在棺木前吻別了爺爺。火化後,他的骨灰罈在家人的陪伴下送到小港的墓園,就放在奶奶的旁邊。
送別的儀式結束了,上計程車前,我摟著媽媽和姊姊放聲大哭。當下我同時感覺到完結與新生,一種暫時只能透過悲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喜悅,我知道我將迎來長達四十年的爺孫關係的2.0版本,爺爺只是換一個地方活著。
返回台北隔天,我拿著爸爸給我們的紅包袋到忠孝新生附近的銀行準備存入爺爺的遺贈。他留給每個孫子八萬多塊,不是多大的數目,換成千元鈔卻仍是厚厚一疊。幾經震盪的2018總算就要過完,天很陰,雲低低的,街上下著一點雨,我從銀行轉入濟南路打算找東西吃,經過一家義式小館,忽然憶起爺爺還能上台北找我們玩的日子,我和姊姊、姊夫以及仍在學步的外甥女陪他在那邊吃過一次飯。
當天爺爺點的是什麼呢?照例是黑咖啡加糖奶,羅宋湯配奶油麵包?他是不是為了帥氣又在室內把墨鏡給戴上了?我在小館前駐足,那一刻,深深感覺到爺爺的存在,他的遺贈不只是剛剛被我存入的遺產,更是他整個精采的人生,和我們分享的每一則記憶。
生命是一門時間的藝術,在我心中,爺爺一直是優游在時間裡的大師。本質上是一場生前告別式的九十九歲生日聚會中,他對在座的族人說:「沒什麼好悲傷的,到時微笑送走。」
在那條漫無止境的時間軌道中,未來將不再產出關於爺爺新的回憶,我們能反覆述說的,是那些已經發生過的故事。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VOL 20)

[告 別] 引用(0)